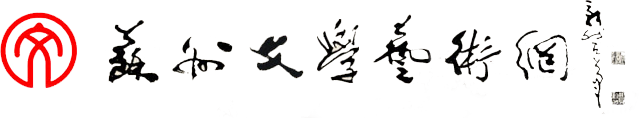
王计兵是近年来涌现出的一个现象级诗人。有关他个人生活经历的宣传报道几乎达到铺天盖地的地步,反而对他的诗歌本身观照不多。近期,陆陆续续读了他的《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两本诗集,总体而言,他的诗显现出了诗之风骨,有态度、有激情、有悲悯、有反思。
一、在群体和个体之间
毋庸讳言,王计兵的诗歌之所以引起关注,首先是因其对外卖骑手形象的精准画像和真情代言,为广大的外卖员群体在文学版图中赢得了一席之地,这确乎是其写作的一大贡献。文学与时代是一种对称关系,可以呈现实相、虚像,乃至位移、变形,但总归要反映、表现现实。世界日新月异,而文学需要有一副消化新生事物的好胃口。但这里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转化问题。写诗犹如酿酒,外在经验不是原封不动地进入诗歌,而是要在心灵的酒窖中经历神秘、复杂的置换,需要动用诗人特定的情感、记忆、灵感乃至幻觉……王计兵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出色地完成了诗意的发酵、蒸馏和提纯,将泥沙俱下的职业经验巧妙地转化为精炼的诗歌语言,规避了此类诗歌易于陷入的无病呻吟和口号式的表面文章。他的成名作《赶时间的人》无疑堪为表率。
首先诗题“赶时间的人”对外卖员形象特点的概括非常精确。在写这篇评论的当口,我正好点了一份外卖,门铃一响我就立刻去开门,但还是晚了一步,门一开只有外卖在地上,外卖员早已赶下一单去了。用“赶时间的人”来形容这一职业打工人的特点,无疑殊为贴切。再看这首诗的炼字。“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一个“赶”字层层递进,有一种重锤一下一下不断加大力度朝下击打的决然。果不其然,结尾他就炼出了这个“锤”字:“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写出了重如千钧的气势和悲壮感。同时整首诗的语气非常急促,在诗行音节的建构中模拟出了外卖员“飞奔”的脚步声,仿佛能够听见他们马不停蹄赶路的急促的呼吸声。在他浓墨重彩的渲染下,风风火火的外卖员形象甚至沾染上了一股子神性:令人联想到脚踩风火轮在空中叱咤疾行的哪吒。
一个外卖员,一如凯鲁亚克《在路上》里的人物,他永远是在路上,看不见终点。在另一首题为《何为远方》的诗中,王计兵将外卖员和流浪汉两相比较:作为路上的风景,流浪汉触发了他的善念,让他有了想捎他一程的想法,但却意外地被谢绝,流浪汉平静的神情让他觉得“自己才是需要被带上一程的人”。紧接着,诗歌写到:“把一个没有终点的人捎上一程/并不能缩短他迷宫般的路程……”这样深刻的反思,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如果说,《赶时间的人》刻画了外卖员的群像,带有公共的普适性,那么这首《何为远方》则凸显出鲜明的私人性,一下子将我们从某个群体的平面拉入孤独个体的内心漩涡。这同样也显示出王计兵的诗歌创作绝不仅仅是“一个外卖员的诗”(诗集《赶时间的人》的副标题)的标签所能概括和遮蔽的。
翻看王计兵的诗,我的脑海中不自禁地闪现出勃莱的一首诗:“从远在外面的无遮的湖泊中心/潜鸟的鸣叫升起来。/那是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的人的呼喊。”(《潜鸟的鸣叫》董继平译)在王计兵的诗中,我能时时听到类似这种“潜鸟的鸣叫”:对于生活、对于故乡、对于亲人的呼喊,以及代替沉默事物发出的呼喊……
“母亲常替一些沉默的事物
发出声音。比如
替几株被风折断的玉米呼天喊地
替一片倒伏的麦苗
痛哭失声”
——(《生前》节选)
二、内生性的写作
王计兵的写作可以归入内生性的写作范畴。他的诗是在长久的生活磨难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诗歌。绝不是通过学一点诗歌技巧就能达到的。我很赞同诗人胡弦的一句诗:“积百凶而得一诗人”(《杜甫故里》)。人生的磨难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成就了一个诗人,往往成为其诗歌写作的丰富矿脉。在送我的诗集扉页上,王计兵写下一句赠语:“生活像一面斜坡/诗歌是陡峭的另一面”。斜坡上的生活,宛如西西弗斯循环往复的永恒劳作,而诗歌恰在其背面熠熠生辉,成为他不断转过身去的支点。
王计兵做过无数的活计:建筑小工、捞沙、开翻斗车、摆地摊、拾荒、开杂货铺、送外卖……仿佛是来自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中的人物——那个废纸回收站的打包工,甚或是赫拉巴尔本人。捷克一代文学大师赫拉巴尔的写作经验可资借鉴,他曾做过推销员、仓库管理员、炼钢工、废纸回收站打包工、舞台布景工等等,这些职业经历同样为他的创作生涯提供了支撑,他说:“生活,在任何地方都要不惜任何代价参与生活。”(刘星灿《赫拉巴尔和他的作品》)
王计兵的诗歌写作是扎根于自身丰厚驳杂的人生经验基础上的,这使得他的诗歌文本天然地远离那种工于辞藻、繁复炫丽、凌空蹈虚的形态,多了种与生活短兵相接的凌厉和质朴。这是从个体心灵和苦难现实的碰撞搏斗中开出的血肉之花。其诗中俯拾皆是的生活细节即是明证。
“一次意外,铁皮锋利的边缘
割断了我右手小指的肌腱
后来,这个小指慢慢弯曲僵硬
仿佛身体上多出来的一个钩子
这很好,方便我悬挂
生活里突然多出来的外卖
那些滚烫或冰凉的外卖
时常挂在钩子上
让我看上去更像是一面行走的墙”
——(《墙》)
这是一首尖锐之诗。一根受伤的手指,令主体感知到身体的异化,在残酷的生活面前“我”被降格为“物”:一面长着钩子、挂满外卖的“行走的墙”。
而在另一首诗中,王计兵为我们奉献了一个更为经典的意象——一只漏气的皮球。
“就差那么一点点
如同一只弹性不佳的皮球
而世界这么大
空气这么多
……
也许生活原本就是这个样子
一只漏了气的皮球更便于携带
我们才会为了一口气
努力地活着”
——(《如果生活》)
王计兵从一只漏气的皮球中看见自己为了一口气而努力活着的样子。这是一次极富诗性的凝视。在那样的一瞬,过往艰难困苦的万千碎片破空而来,凝结成这样一只漏气的皮球。是的,漏气,永不可能被撑满,但也不会因此就“断气”,一种备受摧残、不断挣扎的中间态。这是主体省思的对外投射和返照,足以让我们领略王计兵心灵透视般的“观察”之道。
三、“观察”之道
美国诗人玛丽安·摩尔有一本著名的诗集就叫《观察》。其中有一首专门探讨了为诗之道,她说:“想象的花园里有真实的蟾蜍”(《诗》明迪译)。是的,诗意不是凭空生发的,它应是根植于精确的及物性,如同印象派画家莫奈笔下美如幻觉的《睡莲》,天才的想象力,总是要委身于老老实实的现实“观察”。王计兵敏感而细腻,像一块海绵,他将自己沉浸于生活的乱流之中,目力所及,每每能从司空见惯之处生发别致诗意。他的诗足够真诚,全无一丝矫揉造作。他的诗简明而清晰,硬桥硬马,不耍花招。
他会从一条覆盖薄冰的初冬的河移情到老年的脆弱,意识到那一层薄薄的“表面的坚强”正掩盖着“深处的软弱”(《傍晚,在河边》)。当他坐上回乡的火车,那个背对行驶方向的座位,让他感觉到自己是在“以退行的方式回家”:“仿佛生活的一次退货/一个不被异乡接收的中年人/被退回故乡”(《退行的火车》)。
在送我的另一本诗集扉页上,王计兵写到:“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我仔细翻找了下,出自他的那首《春天》。诗中,他说:“我对四季常青的植物/一直心存芥蒂/而愿意把落叶乔木认作亲人”。他始终在意的是肃杀冬日里瑟瑟发抖的事物。
而王计兵确实写了很多关于“亲人”的诗。比如他写父亲、母亲的诗几乎占了诗集的大半。这部分的诗同样写得精彩而感人,有着巨石压住泉眼的幽咽。
“两个男人像两块木炭
各自守着炉火半边
煤球块偶尔炸裂,啪地一响
夜色深暗
偶尔有过路的车灯从门缝照进来
像是生活伸进来的一根火柴
一张脸皱纹纵横
另一张脸正在皱纹纵横
一条河正在接近另一条河流”
——(《和父亲一起除夕夜守岁》)
像一部纪录片的一个镜头,它恰到好处的明暗处理、光影调色,以及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留白,让这首诗用沉潜的低音抵达了振聋发聩的境地。王计兵对于苦难的书写,显现出足够的克制。在他状态最好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卓然超拔的气象,一种孤冷的凛冽:
“从人民路拐进幸福大街
挂在腰带上的瓦刀
不停地拍打我的臀部
十几年了
也没有把我砌成一堵墙
……
满大街都是手无寸铁的人
让我突然产生出优越感
一个又一个城市
允许我名正言顺地携带‘刀具’”
——(《瓦刀》)
我很喜欢这首诗结尾的“图穷匕见”。像一个被遗忘的刺客走在这荒凉的人间。在生活的暴君面前,时时涌动一颗不臣之心。就像另一首题为《寂静》的诗中,结尾突然冒出的一句——“我以为一条鱼/就能救活一个营养不良的时代”,猝然给生活以旁逸斜出的一击。
回到这篇文章的标题:“像一小撮火药,带着隐约的危险。”(王计兵《农村的房子已越建越高》)我更欣赏王计兵诗歌中这样一类的句子,凝练、锋利,不动声色,又不怒自威。我其实想表达的是,王计兵的诗有烟火气,也有火药味,某种程度上正是这“隐约”的火药味,令他的诗歌有了不同于流俗的潜在特质。祝福王计兵,祝愿他在未来的诗歌之路上能够呈现出更多的变化和可能。
(杨隐,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