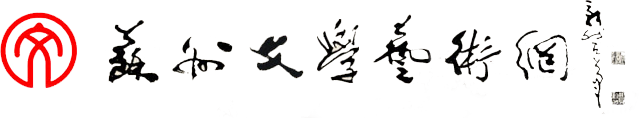
传承与探索发展是当代昆剧的使命。以此而言,新编移植改编昆剧应当得到鼓励,其中之得失也应及时总结。作为一次尝试,昆山当代昆剧院编创的昆剧《西厢记》首演后引发不少反响,褒贬杂陈,值得肯定处与有待改进处并存。
戏剧作品一旦公演,其效应是作品和观众共同创造的。从首演剧场反响来看,当代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对改编《西厢记》并无隔膜感,从头至尾都津津有味地观看,不时爆发出喝彩声和掌声。昆剧《西厢记》的核心戏段一个非常成功的地方是富有“戏中戏”,情、趣、理交织,并借此悄然勾勒出剧中主要人物的鲜明性格。这个核心戏段自老夫人悔婚始,至红娘于老夫人面前点明莺莺、张生已“生米做成熟饭”终。张生书信搬救兵解普救寺之围,却换来老夫人不守诺言悔婚,让莺莺与张生兄妹相称,这如一记重锤,同时击穿了张生、莺莺和红娘的心理底线,平地惊雷,顷刻间给戏带来三重戏剧矛盾:一重是于理不通,毁弃诺言,张生极端委屈憋屈,莺莺歉疚羞愧,红娘憋闷义愤,皆理失意乱;二重是于情不容,一言相阻,张生钟情难托、深情难忘,莺莺芳心萌动、情难自抑,红娘憾意难消,三人困于情义,皆不甘心;三重是于趣有致,情急之下,张生猴急呆萌,莺莺半推半就,红娘机智俏皮,皆妙不可言。有趣的是,这三重戏都经由红娘这个枢纽点来串联。
在寻理展情中,张生气难平、情难寄中猴急呆萌、富有才情的性格尽现,莺莺内疚又怀春的娇羞娇媚、有情有义也展现得淋漓尽致。而红娘看不惯老夫人的无端毁约,同情张生,也企望小姐有个好归宿,有意玉成好事,但她只是个地位低下的丫鬟,既要面对老夫人的权威蛮横和小姐的羞怯摇摆,又要面对张生的不平、性急和不得法,正直有义的红娘能做的就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在权威、羞怯和呆急中巧妙周旋,机智应对。对老夫人,她面顺心非,对小姐,她心如明镜,呵护中深有洞悉,顾及面子中有引导,对张生,她同情礼貌中有暗示指点。这一过程使这个戏充满戏剧性。
而张生与莺莺的感情戏本就是《西厢记》的主线。从惊艳、遭围、许诺、反悔、怨愤、暗会,到老夫人默认、设限,最后张生赶考,完全是中国叙事文学中一个常见的难题型求婚原型故事,但这个故事因中国传统社会的家长制权力体制和血缘伦理体系等的文化、观念和情感背景,自有其打动中国观众的魅力基因。故而,这个戏的戏剧矛盾、结构、人物塑造等都围绕这一主线铺陈展开,张生和莺莺相遇相爱的波澜曲折,始终紧紧拨动着观众的心弦。情感戏是《西厢记》精彩性的基石。
有意思的是,这段戏中,老夫人、莺莺和张生的纠葛与戏份,是在红娘的串联周旋下被盘活的。他们的性格在与红娘的互动碰撞中被雕琢得更加棱角分明,在红娘的机智乖巧正直面前,老夫人的蒙在鼓里,莺莺的欲迎还拒,张生的急不得法、狼狈跳墙,都被反衬出颇有喜剧性的滑稽感,令人忍俊不禁。另外,诸如老夫人悔约后张生莺莺感情如何发展的悬念、红娘要张生跳墙会小姐的捉弄、张生与莺莺感情发展中的误会,等等,这些手法的运用,更凸显了《西厢记》的喜剧性。可以说,红娘是中国传统戏剧中最光彩照人的“第一丫鬟”,皆缘于其聪慧有趣,这个形象提升了该剧的艺术性,增加了该剧的趣味性。
这段核心戏传承了元杂剧《西厢记》中的精华,但有所取舍,调动了各种舞台要素使戏之理、情、趣三重戏剧矛盾和效果更加集中鲜明,使戏剧节奏加快、人物性格更为突出,面上的戏和心理戏交织,戏中有戏,这是这个改编版的成功之处。但不管怎么说,杂剧《西厢记》中妙趣横生、心理戏丰富的“拷红”一出被缩水简化,并不明智。
首演之后,对《西厢记》的质疑也有不少,主要意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认为改编不成功,现在的演出好的吸引人的都是原著优秀;二是认为其有些剧情和场面处理背离了昆剧传统的虚实结合、诗情写意的精神;三是认为该戏存在迎合市场的媚俗倾向。
对于《西厢记》的改编,昆山当代昆剧院组建了阵容不俗的专家团队,下了很多功夫,首演也获得了良好的剧场效应,说明其改编在集中突出主要剧情与人物等方面是有其成功之处的,当然也存在不足,这一点上文已作分析。至于断言当代人没本事改编,则是无稽之谈,青春版《牡丹亭》就是一个成功改编的经典例证。更有道理的是第二种批评。南昆保留了“水磨调”的传统,自有其兰韵幽香、清丽优雅、含蓄蕴藉的苏州美学风范,这也是正宗正统正派的苏州昆曲风格。以此观之,编导为了迎合想象中的青年观众和市场,将张生与莺莺的夜会处理得比较写实露骨,让张生行为举止沾染上些许轻浮之气,将当代网络语言掺入台词,既有损张生这个读书人清俊儒雅的形象,更不符合苏州昆曲本该坚守的唯美写意的美学风格,应借鉴《牡丹亭》等用舞蹈或暗场的含蓄留白方式来处理。台词上引入网言网语也与本该贯穿全剧的雅韵风格显得格格不入、突兀庸俗,编导以为如此塑造张生、处理台词更能吸引青年观众,实则误解了市场,低估了青年观众的审美水准。
好在戏曲作品可以听取各方有益意见,边演边改,相信昆昆版《西厢记》能在坚守苏昆美学原则与真正的艺术创造中走向成功!